似乎和一種鮮紅的顏色永遠聯系在一起,鮮紅的外套、雪白的頭發,形成極強烈的反差。盡管伯恩斯坦不會穿著鮮紅的禮服上臺,但紅色似乎成了他永遠的象征。它意味著激情、詩意、泛濫的浪漫和隱含在微笑中的睿智的幽默與俏皮。
伯恩斯坦(1918---1990)
應該說,自富特文和托斯卡尼尼之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卡拉揚與伯恩斯坦構成了新的兩極:卡拉揚把理性結構的營造推向極致,伯恩斯坦把感性的情感刻劃推向極致。相對于卡拉揚營造的一個個精致的空間,伯恩斯則以他充滿激情的生命為我們劃出了一道道迷人的弧線。
以下有兩段文字介紹伯恩斯坦:
在20世紀中葉后崛起的指揮大師中,如果說卡揚是歐洲古典樂壇的帝王,那么拍恩斯坦便是北美這塊新大陸的最高權威。正是伯恩斯坦的出現,使得北美這塊新大陸有了足以與大西洋彼岸的古老歐洲抗衡的音樂代言人。
指揮藝術不僅是伯恩斯坦音樂天才的最佳用武之地,也是他藝術個性的最典型體現。他一方面將古典音樂的精神遺產與新大陸所孕育的旺盛的生命力融為一體,將浪漫主義的闡釋風格推到了極致,同時又不斷地從深厚的歐洲傳統中汲取精神營養,尋找音樂上的精神歸宿。
這種指揮風格并非在所有古典作曲家的作品中都能取得成功。像當代絕大多數指揮家一樣,貝多芬的作品在伯恩斯坦的指揮曲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某些重大的、具有紀念意義的場合,伯恩斯坦是以貝多芬作品在當代的最佳闡釋者之一的形象出現的。如在1970年紀念貝多芬誕辰200周年之際,奧地利政府選定伯恩斯坦在維也納歌劇院指揮《菲岱里奧》;1989年圣誕節,為慶祝柏林墻的拆倒,伯恩斯坦指揮了第九交響曲。他先后為CBS公司和DG公司各錄制了一套貝多芬交響曲全集,后一套是在貝多芬的主要居住城市維也納與作為音樂傳統化身的維也納愛樂樂團合作錄制的,但在評論家保羅*亨利*朗格看來,伯恩斯坦對貝多芬交響曲中的闡釋“才華多于趣味”。 伯恩斯坦氣質中過于浪漫化、主觀化的成分使他缺少貝多芬作品所要求的均衡感及自我約束能力。當然,第三《英雄》交響曲是一個優秀的例外,伯恩斯坦對這部交響曲的闡釋無疑屬于最杰出之列,在這里,伯恩斯坦的音樂理解力,他的充沛的熱情以及對紀念碑式宏偉氣概的追求使他真正捕捉到了貝多芬精神的核心。
與伯恩斯坦的指揮風格不能契合的另一位作曲家是布魯克納。伯恩斯坦浪漫的指揮風格照理應該適合這位晚期浪漫派作曲大師那些內涵豐富、精神境界宏大的交響曲,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伯恩斯坦很少指揮布魯克納的作品,只是對第九交響曲情有獨鐘,先后留下了兩個錄音。理查德*奧斯本在聽過后一個也就是指揮維也納愛樂樂團為DG公司錄制的版本后作也的評價很有代表性:“我認為伯恩斯坦熱愛這部作品但不理解它。”另一位評論家勞倫斯*B*約翰遜指出,布魯克納的第九交響曲“意味著某種精神企求,這種企求在伯恩斯坦指揮的馬勒作品中意味斗爭。然而在布魯克納作品中并沒有斗爭,有的只是渴望與人性,以及對上帝的贊美。”
這各情況的根源在于新大陸的文化與歐洲傳統音樂文化的差異。約翰*L*霍爾姆斯在出版于八十年代的《唱片是的指揮家》一書中這樣概括伯恩斯坦的指揮成就:“伯恩斯坦是迄今為止最引人注目、最有造詣的美國指揮家,他多方面的才華及音樂修養必須給予高度評價,然而他在偉大的指揮家中處于什么樣的地位卻仍是一個問題。對于世界是其他地方的人來說,伯恩斯坦身上體現了美國文化的許多為人們熟悉的特征:過分展現的魅力與光彩,感情是自我約束的缺乏使得他難以將熱情與夸張的渲染區分開來。”
然而,伯恩斯坦身上所體現出的美國文化特征以及得天獨厚的條件,造就了一種高度個性化的、激情澎湃、豐富復雜的指揮風格,這種風格在海頓、馬勒、斯特拉文斯基中得到了最充分發揮。這三位作曲家分別屬于古典、浪漫和現代時期,乍看起來似乎沒有多少共同之處,但正如伯恩斯坦本人認識到的那樣,他們三人都可以被看作是最細膩的民間音樂家,也就是說,他們都將自己的創作深深植根于民間音樂傳統,將民間音樂素材納入到高度發達藝術的語言中,同時又不失卻民間音樂樸素自然的特征。這在某種程度上正是伯恩
斯坦音樂觀、人生觀的集中體現。
對于伯恩斯坦來說“民間”一詞有著比人們通常理解的遠為豐富和深刻的含義,它就本質而言是指人民和大眾。正如戴維*希夫深刻斷言的:“他們(指伯恩斯坦)相信公眾。音樂是為大眾、為所有人創作的,而不是為了音樂家和少數有教養的音樂會聽眾創作的。音樂喜劇是對公眾說話的、戲劇、電影和電視是能觸及到億萬人民的媒體-‘億萬人民’,這個貝多芬第九交響曲中合唱隊唱出的詞匯,是伯恩斯坦的信條。”伯恩斯坦從海頓、馬勒、斯特拉文斯基中尋找到的是過去與現在、經典與大眾以及不同文化間在精神上的溝通、融合。評論家戴維*赫維茨在美國《CD評論》雜志1993年7月號上評論索尼唱片公司在“皇家版”系列中重新發行的伯恩斯坦指揮海頓交響曲錄音(“巴黎”和“倫敦”交響曲)時認為:“伯恩斯坦”是一位最大的海頓作品指揮家。就象在馬勒作品中一樣,海頓的音樂中的某些東西與這位指揮家的氣質相契合。事實上,海頓與馬勒也頗有共同之處。在音樂上他們都體現了兼收并蓄的特征,將巴羅克時代的對位技巧與民間曲調、鄉村舞曲及進行曲輕而易舉地融為一爐。兩位作曲家都是配器藝術的積極革新者,二人都有極為豐富的幽默感(這一點在馬勒的作品中經常被忽視,而在海頓的作品中又常被誤解)。所有的這一切在伯恩斯坦的闡釋中都有鮮明的呈現,不過,我們首先感覺到的是演奏中包含的巨大的活力。”伯恩斯坦將海頓完全變成了當代人心目中的海頓這種闡釋與那種回歸歷史的本真演奏或古樂運動格格不入。古樂器運動倡導者們用完全或盡量貼近海頓時代的樂隊規模、表現手法和感情將音樂和聽眾拉回到過去,而伯恩斯坦則完全以現代人的眼光、要求、熱情和理解力,用龐大的現代管弦樂隊將海頓音樂中的力量和美、熱情和幽默表達的淋漓盡致。新大陸音樂巨人的充沛活力與熱情并沒有被歐洲十八世紀宮庭的繁文褥節所束縛,相反,舊式的小步舞那種拘謹平緩的舞步被新大陸崛起的現代人瀟灑豪邁的步伐取代。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伯恩斯坦在海頓作品闡釋上的成功反映了新的土地、新的民族以及新的時代所具有的力量和自信。當代最杰出的海頓研究權威H.C.賓漢*蘭登斷言:“伯恩斯坦即使不是我們今日擁有的海頓音樂的最偉大的闡釋者,也是最偉大的之一,無論在美國還是歐洲。”
在馬勒作品闡釋上伯恩斯坦完全找到了自己的存在,他已經成了馬勒精神的化身。
與海頓相比,馬勒的個性和精神世界與伯恩斯坦有著更多的相同之處。馬勒精神世界中種種難以調和的矛盾在伯恩斯坦精神中也有著對應和共鳴:創造者與闡釋者,猶太教與基督教信念,信仰與懷疑,天真與世故……伯恩斯坦的闡釋突出和強化了馬勒精神世界中的對立與矛盾,使馬勒的作品真正成為現代人的精神寫照。正是與馬勒精神的這種天然契合,使伯恩斯坦成為馬勒音樂在我們時代的最偉大的闡釋者。
像馬勒一樣,伯恩斯坦也融指揮才能與作曲才華于一身。這種情況自近代指揮藝術成為一門獨立的專業起并不多見。馬勒和理查*施特勞斯體現了偉大的古典-浪漫傳統在其即將走向終結時輝煌的回光反照,而伯恩斯坦則顯示了新大陸在音樂上擁有的巨大潛能。他以自己用之不竭的熱情與精力將音樂帶給億萬大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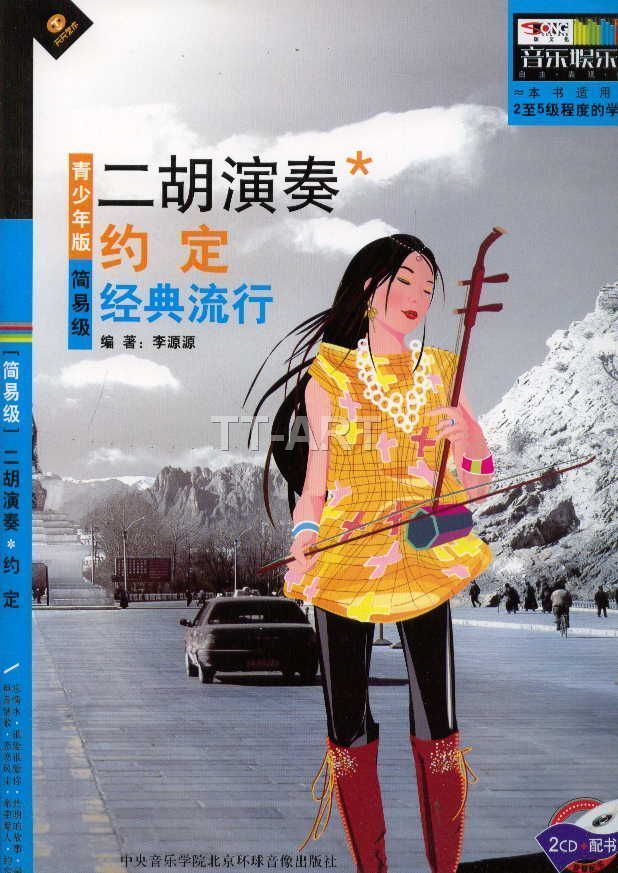

 京公網安備 11011202001714號
京公網安備 11011202001714號